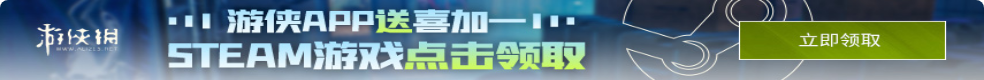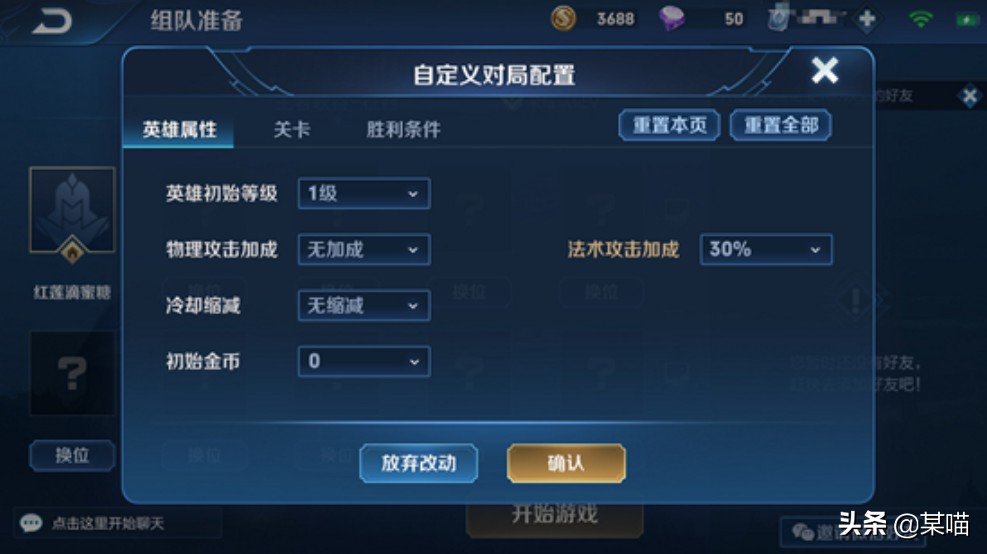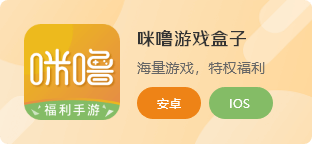清晨6点的南京江宁区稻田里,27岁的植保员林晓芸蹲在埂边,鼻尖几乎贴到稻叶,指尖捏着一片带虫洞的叶子——她的放大镜里,3头稻飞虱正沿着叶脉爬动,这是她今天数的第147头虫子。
“数虫子能当工作?”路过的村民张婶扛着锄头笑,“我种了20年地,从没见过有人蹲在田里‘数虫子玩’。”但林晓芸的记数本上,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:“稻飞虱:第3块田,每百株128头;稻纵卷叶螟:第5块田,每平方米6头……”这些数字不是“玩”,是给稻田开“药方”的关键。
“以前治虫靠‘经验’——看叶子有洞就打药,现在得靠‘数据’。”林晓芸翻出手机里的虫情阈值表,“比如稻飞虱,每百株超过200头才要防治,低于这个数打药就是浪费。”她记得去年夏天,有户农户急着打药,说“地里有虫子就得杀”,她蹲在田里数了1小时,算出虫口密度只有160头,劝住了农户——最后那片田没打药,稻子反而长得更壮,农户后来专门来找她“学数虫子”。
这群“数虫人”里,既有刚毕业的植保专业学生,也有做了5年的“老技术员”。25岁的吴磊是团队里的“耐力担当”,上个月在玉米地数玉米螟,他蹲了3个小时,数完1亩地的虫洞,站起来时腿麻得差点摔倒:“夏天田里40度,蚊子围着脸转,可要是数错了一个数字,可能就会让农户多打一次药——这不是‘数虫子’,是在给土地‘把脉’。”
他们的工具里,既有传统的放大镜、记数本,也有智能虫情测报灯——晚上灯一亮,趋光性害虫会飞过来,第二天他们要把诱捕到的虫子分类、记数,再和田间数的数字对比。“机器能帮着‘抓虫子’,但‘数清楚虫子的脾气’还得靠人。”吴磊举着一只诱捕到的棉铃虫,“比如这只,翅膀上有损伤,说明是从隔壁村飞过来的,得赶紧通知周边农户防迁飞。”
傍晚时分,林晓芸结束了一天的工作,把记数本塞进帆布包。她抬头望着连片的稻田,风里飘来稻花香:“昨天有个小朋友问我,‘姐姐你数虫子累吗?’我告诉他,每数一头虫子,就是在帮稻田‘挡住’一次多余的农药——你看,那些长得直挺挺的稻子,就是我们数出来的‘成果’。”
在农业农村部的“精准植保”试点名单里,南京这群“数虫人”的工作被写进了案例。他们蹲在田里的身影,其实是农业现代化的“微观注脚”——以前靠“经验”种地,现在靠“数据”种地;以前“打药治虫”,现在“数虫治虫”。而那些写在记数本上的数字,最终都会变成给土地的“健康报告”,变成农户口袋里的“省钱账单”,变成餐桌上更安全的粮食。
夕阳把林晓芸的影子拉得很长,她转身走向田边的小路,背包里的记数本哗哗翻页——明天,她还要来数虫子,因为她知道,每一个数字背后,都是土地的期待。